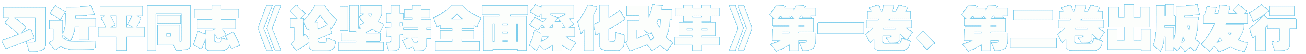先驱者遗产 重温李大钊的光辉篇章

李大钊像。(资料图片)

1919年9月、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6卷第5、6号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我国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资料图片)
李大钊不仅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和创始人,同时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一名先锋战士,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他存世的文集中留下了很多经典篇章,时至今日依然闪耀着历史的光芒。
率先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
马克思主义最早是在19世纪70年代传入中国的。当时一些中国留学生与外交官远赴欧洲各国,在其工作记录以及日记中出现了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如王韬的笔记《普法战纪》描述了发生在法国的巴黎公社运动。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新兴的一些报刊在报道西方思想动态时也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理论,1899年《万国公报》刊登蔡尔康的《大同学》,被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最早介绍。20世纪初期留日学生群体翻译的日本社会主义著作高达二十余种。梁启超、孙中山都曾将马克思主义作为重要内容吸收进自己的著作。
李大钊在就读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时,就参加留日学生的爱国运动,并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投身新文化运动,1918年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李大钊备受鼓舞,开始专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成为十月革命后中国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这三篇文章的发表,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先导的作用。
1918年7月《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发表,李大钊指出俄国革命是20世纪世界革命的先声,他号召国人迎接自由人道的新俄罗斯和世界新文明的曙光,以适应“世界的新潮流”。李大钊认识到俄国十月革命与法国革命性质不同,俄国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当然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还有一定浪漫主义成分,认为“俄罗斯革命之成功,即俄罗斯青年之胜利,亦即俄罗斯社会的诗人灵魂之胜利也”。1918年底,李大钊连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首次把俄国革命与马克思、列宁联系起来,认识到布尔什维主义就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主义。1919年9月,《新青年》6卷5号刊出“马克思主义专号”,卷首刊载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进行了更为系统的介绍和评价,明确将马克思主义看成“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分为历史论、经济论和政策论,而唯物史观则是整个体系的基础。
从1920年起,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史学系、经济系和法律系开设了“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式列入大学教学课程。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李大钊彻底完成了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一书指出:“李(大钊)先生是研究历史最有成绩的人,也是唯物史观最彻底最先倡导的人;今日中国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的思想这样澎湃,可说都是先生立其基,导其先河;先生可为先知先觉,其思想之影响及重要可以知矣。”
率先澄清“主义”的本质问题
马克思主义能够被中国社会所接受,在众多学说和方案中脱颖而出,除了其自身的真理性、科学性与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高度契合之外,先驱者有意的推动、宣介和斗争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使得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处于调和状态的各种派别的立场和主张更加清晰化了,胡适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公开表达对马克思主义的质疑和攻讦,不愿意看到新文化运动发展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运动。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劝说人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并攻击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中国问题要作“根本解决”的主张是“自欺欺人”的梦话,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攻击阶级斗争学说会“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须有的惨剧”。
针对胡适的观点,李大钊于1919年8月撰写《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进行批驳。他声明“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宣传理想的主义与研究实际的问题“是交相为用的”,“并行不悖的”。针对胡适反对“根本解决”的主张,指出:“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没有生机的社会,“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就能实现,也不知迟了多少时期。”
之后,胡适又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和《四论问题与主义》,李大钊则写下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予以回应。在说服对手不要“因噎废食”的同时,他并不否认在问题的“根本解决之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这里的准备活动就包括了有组织有目的的各种实践。之后,李大钊还参与了同张东荪、梁启超等人的论战,批驳了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论调,并同以黄凌霜等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展开斗争,批驳了“绝对自由观”。
率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和原则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是毛泽东同志在1938年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明确提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应该说,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主要在中国共产党创立初期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的阶段。但马克思主义传播从一开始就明显地带有解决中国社会矛盾的任务,李大钊等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时不可能认识不到这一点。他们从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就将其视为理论与方法统一的世界观,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将其作为观察和改造国家的工具。《再论问题与主义》中已经触及这个问题:“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
李大钊不仅具有“中国化”的清晰自觉,也提出一些具体方法和原则。一是不能“偏于纸上空谈”,要“向实际的方面去作”“细细的研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二是“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以研究怎样成了中国今日政治经济的情状,我们应该怎样去作民族独立的运动,把中国从列强压迫之下救济出来”。三是要与工农运动相结合,“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四是发动中国最广大的农民,“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
李大钊生活的那个时代,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还处于斗争经验不足的初创时期,他本人不幸过早牺牲,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很多没有深入,但其思想见解影响了身边的毛泽东等人,启发他们在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过程中寻找到了一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道路。
率先提出“中华民族之复活”的思想
李大钊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心怀复活更生的中华民族,向往传统思想中的天下大同。正如他的诗句“何当痛饮黄龙府,高筑神州风雨楼”所言,民族复兴是李大钊毕生的宏愿,是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动力,也是共产主义理想与民族独立要求、历史文化传统高度契合的所在。
在1916年发表的《青春》和《〈晨〉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等文章中,李大钊认为宇宙是无始无终的自然存在,宇宙及所包含的每个个体都处于不断变化新陈代谢之中:“有生即有死,有盛即有衰,有阴即有阳,有否即有泰,又剥即有复,有屈即有信,有消即有长,有盈即有虚,有吉即有凶,有祸即有福,有青春即有白首,有健壮即有颓老”,国家和民族一样都是有生命的,也都有年轻、年老之别,而当前的中华民族已是白首之民族,已失去了生命的活力,处于濒灭垂死之中。那么希望何在?李大钊答:“吾族今后之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中华民族通过凤凰涅槃获得重生,重新获得生命活力的中华就是青春中华,青年则应该承担起历史的责任,成为担当再造的主体。在《第三》《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等文章中,他对东西方文明进行了系统比较,认为东方文明是主静的文明、灵的文明,而西方文明是主动的文明、肉的文明。而中国未来追求的应该是调和双方弊端、吸取优长的“第三文明”“乃灵肉一致之文明、理想之文明、向上之文明也”。
李大钊的这一思想有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影子,代表了一战之后中国知识分子调和东西方文化的尝试。然而俄国十月革命之前,这种思想只是停留在哲学和思想层面,是十月革命加速了李大钊思想的转变,使得李大钊找到了青春中华、“第三文明”的实现路径。他敬告国人:“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世界中将来能创造一兼东西方文明特质、欧亚民族天才之世界新文明者,盖舍俄罗斯人莫属”。十月革命后的俄国道路,正是能够彻底摆脱东西方危机的“第三文明”。
李大钊将民族生命喻为回环于宽阔与逼狭的境界之间的长江大河,相信民族雄健的精神能够冲过艰难险阻的境界。他在《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一文中说:“中华民族现在所逢的史路,是一段崎岖险阻的道路……我们应该拿出雄健的精神,高唱着进行的曲调,在这悲壮歌声中,走过这崎岖险阻的道路。”当前中华民族正在驶过新的历史三峡,这条路充满希望和机遇,也充满风险和挑战。在李大钊等革命先烈精神鼓舞下,我们一定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沿着先辈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林水)
中国传媒网摘编:亓淦玉 |